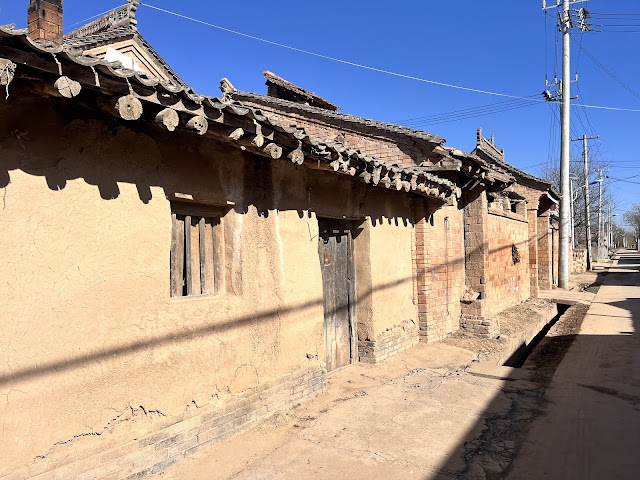迷失香港(一)
终于去了趟香港。 香港和我想像中不同,却又相同。朋友问,走在那些电影里的街道上,是什么感觉?我说蛮好的,感觉和周润发林青霞突然成了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他问有没有幻灭,大概以为我会为那些夹杂在现代化高楼大厦中的破败建筑所惊异。当然没有,我几岁了都,好歹此前也见了一点世面。 但你要说去之前我头脑中的香港就是那样的,那也不符合事实。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文章,说港府有意将九龙城寨打造成旅游景点。问我鱼姐,要怎么去,我想去看。我挺喜欢那个电影,大概因为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样,对于业已逝去的旧香港怀着多多少少的眷恋。电影里的九龙城寨,破败、逼仄,像末日废土。结尾几个新生代站在高处的雨篷上远望,你说不上导演是在致敬哥谭的蝙蝠侠还是哥谭的小丑。我鱼姐很不客气地说,九龙城寨拆了很多年了,哪儿有的看。后来弄明白,所谓的景点,不过是搭在机场旁边的模型。我当然也没看到,到达和离开时,都忘得一干二净。 我住在佐敦的一家旅舍,三百多块,大概四五个平方。开门一步就到床,床的三面靠墙。我在峰哥的视频里看到过这样的房间,却是第一次住。我正用密码开门,老板娘笑着说,香港就是这样寸土寸金的,没办法。我也笑回,听说了。通过booking的评论区我知道房间很小,但对于这种布局没有心理准备,关上门后,不仅有些哑然失笑。好在房间小是小,还有独立卫生间,长在进门右手。那房间其实订得很仓促,没有规划,看着交通便利,并不知道周围有什么。在那个逼仄的施舍单人床上躺下来打开地图,才发现,不远处是传说中的维多利亚港,而另一个方向不远是传说中的旺角。 我是真不爱做攻略,加上九月以来一直为了父母的问题辗转流离,做好了去不成的准备。临到跟前才问我哥,能不能回家替换我照顾父母,他说可以。你知道吧,这本来也没什么好问的,早就说好的事,只是后来我和他隔网对吵一架,怕他耍脾气不回。实际哪儿能呢,人家六十多岁的人了,能跟我一小孩一般见识嘛!于是时间仓促,加上我鱼姐非常热心给我推荐好吃的好玩的地方,我只需要把她发的消息Pin上墙,更懒得自己筹划。我打趣無名,怎么你跟香港不熟吗,光看热闹,也不给些意见。她哈哈笑,说不知道应该推荐那里,这就去YouTube帮我找。我说打住,想要的是你心心念念的香港,不是别人的,那样的攻略我会自己去看。不然你讲讲你想吃什么,我帮你吃点好了。她想吃叉烧饭、叉烧面、叉烧包。我没吃过叉烧,提起来这两个字,只想到黄秋生演的那个电影...